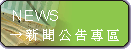辯論-代理孕母
[E]
[X]
辯論-代理孕母
[E]
[X]
定義
目前的代理孕母可分成兩類。
一是由於不孕的女性想要孩子,經由第三者同意後,利用丈夫的精子讓第三者女性受孕,且雙方訂下契約,孩子出生後第三者須放棄親權,並交由男性那方撫養──此類是精子是別人的,卵子是第三者的。
二是指子宮因為某些原因造成缺陷,但是排卵功能正常的女性,取出男性精子和女性卵子在體外授精後,再將受精卵植入第三者完成妊娠、生產階段。
前言
隨著生殖科技的進步,四十多年前開始有了人工受精的技術,此時期的代理孕母雖不必與委託人發生關係,但嬰兒的DNA有一半來自孕母的卵,一半來自委託男性的精子。這樣的狀況,嬰兒與孕母有血緣關係,因此出生後很難割捨,訴訟糾紛迭起,法官也十分難判決這樣的案例。
二十年前試管嬰兒技術成熟,又轉入一個新的形勢。在這之後,委託方的夫妻可以先用自己的精子與卵子在體外﹝試管中﹞受精,再將受精卵植入代理孕母的體內。這時代理孕母與子宮內的胎兒完全無血緣關係,這種做法成為今天的主流,在英國已合法,行情是15,000英鎊;美國也有少數幾個州立法通過,行情是10,000美元。今天你只要上網,輸入Surrogate mother,就可找到一堆網站,有的是誠徵代理孕母的仲介公司,有的是針對不孕夫妻的廣告。在這琳瑯滿目的宣傳網頁下,我們要思考代理孕母的做法是否合理。
嬰兒
1987 Mary Beth Whitehead接受William and Elizabeth Sterns夫婦委託,以一萬美元代價,使用Stern的精子,替Stern夫婦生下Baby M。生產後Whitehead反悔,拒絕接受酬金,也不願將孩子交給Stern夫婦,Stern夫婦因此告她背信,產生了Baby M案。此案Whitehead敗訴,法官Sorkow將Baby M判給了Stern夫婦。
法官把Baby M判給Stern夫婦的原因,不是基於他們與Whitehead所訂的契約,而是因為中產階級的Sterns夫婦比勞工階級的Whitehead能夠提供Baby M更好的「物質、社會、及道德環境」。
更有意思的是法官不但把Baby M判給了Stern,還說Mr Stone「不能買屬於自己的東西(He can not purchase what is really his)」。聽起來好像是︰Baby M既然屬於Stern,他當然沒有理由向Whitehead買她,所以原來約定的一萬美金也該免了。
我國情況
正如立法委員沈富雄在1997. 9. 26立法院公聽會上所說︰男人如果要Whitehead式的代理懷孕的話,只要討個小老婆或者在外面生一個就行了,還搞什麼代理懷孕?因為我們的法律保障非婚生子女的權利,男人在外面生的孩子與婚生子女在財產及身份地位上享有相同的權利,妻子無權拒絕認養。這樣的安排是傳統多妻及納妾的遺跡,表面上的理由是孩子無辜,法律應當保障其權益,實際上等於縱容男人在外面生養孩子。在強大的父權體制下,生育是女人的天職(而且生了女兒還不算),所以除了法律保障,妻子也自認不能生育有虧職守,而不敢拒絕丈夫在外面生養孩子,說不定有人還會幫忙丈夫安排借腹生子。有這樣替男人設想周到的法律,以及與之應合的社會價值及行為規範,情況真一如沈富雄所言︰還需要什麼代理孕母?
法令方面,我國原本已有「人工生殖技術倫理指導綱領」及「人工協助生殖管理辦法」規範醫療生殖行為。在「人工協助生殖管理辦法」中雖然明令禁止代理孕母,但試管嬰兒已開放執行,只不過依規定試管嬰兒在受精之後,要植入妻的子宮懷孕生產。如此一來卵巢功能正常但沒有子宮的女性,就不能利用試管嬰兒技術達到做母親的目的,因此新法乙案打算「適度開放代理孕母」──也就是開放夫妻提供精、卵,由第三者代替懷孕式的代理孕母。
倫理觀念衝突
首先,先反省一下運用這項先反省一下運用這項技術的動機-生兒育女。誠如衛生署人工生殖倫理綱領所宣稱的,生兒育女是人類「最基本的欲求與需要」。因此,以它為動機而尋求醫學的協助,可以說是無可厚非的。不過,人們必須分辨一件事情,那就是:這項最基本欲求與需要的對象是一個人、一個禮物,而不是某種可以讓人佔有、讓人志在必得的貨物。人與貨物最大的不同是,貨物可以完全任人支配,它的價值隨著對人實用與否而定。至於人則不可能被支配,也不能被佔有,人獨特的價值與尊嚴更不能以實用與否來衡量。事實上,任何人的價值都不能用實用來衡量。因為「實用與否」是貨物的價值尺度,不是人的。人,不論有怎樣的聰明才智、身世背景,都應該被當人看。優生學最大的問題並不在於定義優劣時容易有所偏差,而是在於它背後那種只看重外表價值,而不把人當人看的心態。
人固然可以盼望生兒育女,但這並不表示人有權利非「得到」孩子不可,尤其當所有的使用方法會傷害夫妻或者親子之間該有的「仁」的關係時。反過來看,任何孩子卻都有被父母當人看的權利。好比說,他有權知道好能認同他的來源,他也有權被他的父母認同,最後,他更有權得到父母的愛,不論他的智商是高是低,他的身體是健康或是殘疾。
從「仁者,人也」的倫理原則以及上述孩子的權利出發,代理孕母是否合乎倫理,還必須符合以下四個條件。
1.委託代理孕母必須是在沒有任何其它辦法下的救濟手段。
通常包含了婦女子宮因病切除;或者子宮雖然尚在,卵巢也能排卵,然而由於過去有自發性流產、小產或其它嚴重病變,經醫師勸告不宜懷孕者。這些情形就是婦女無法以自己的子宮孕育胎兒的狀況,此時委託代理孕母是情有可原的作法。如果婦女身心各方面的功能都很正常,但卻因為事業或嫌麻煩等理由,而想請別人替自己懷孕,這就比較有問題。懷胎九個月的「共生親密」為母子之間,甚至父子之間的感情極為重要,父母如果能建立這個感情而不去建立,基本上便錯失了孩子生命初期很重要的一個階段。
而且,作父母的如果輕易因為其它理由而不願意在這重要時刻為兒女付出,不禁令人質疑,他們是否已準備好為人父母?有很多東西也許都可以用金錢去換取。然而,有些東西是不能替代的,更不能用金錢買到。一對父母若不願花時間給孩子,就不能建立自己與孩子的親密關係。孩子有多少時間由別人照顧,父母就失去多少與孩子親密共處的機會。吝於付出心力的父母,不但疏忽了愛兒女的責任,也剝奪了兒女被愛的權利。
2.委託夫妻必須使用自己的精卵。
不少單身女子也開始有一種「不要結婚,但卻要有自己寶寶」的風尚。然而,捐贈配子的作法是否合乎「仁」的原則。時代週刊的記者曾經問道:「有誰見過一個孩子高興不知道自己的老爸是誰?」很顯然,選擇這樣的人工生殖方式是有意阻絕孩子的親子認同。此外,若替人懷孕者所使用的是自己的卵子,那麼,這個婦女便是清楚地將生育與養育分裂開來。這種作法不論是為了什麼理由,都割斷了原本不容割斷的親子關係,更何況這通常是為了錢──那麼人們生兒育女的動機會產生深刻的改變,「從願望有孩子本身到願望有孩子是因為他們能夠提供某種好處」。
據報載,臺灣已有許多大學生暑假靠賣精卵「打工」賺錢,便是清楚的例子。這樣的作法不僅阻絕孩子的自我認同,而且將人際關係物質化,嚴重地違反的「仁」的原則。
3.所使用的人工生殖方法不可以任意傷害受精卵或胚胎。
有人也許會說,受精卵或胚胎是不是人仍有許多爭論。然而,毫無疑問的,受精卵已是在連續發展過程中的初期人類生命。這些生命雖然還不具人形,但是,同一個人,同一個生命已在存在的出發點上,以驚人的速度以及令人驚嘆的方式成長茁壯。我們沒。我們沒有理由把胚胎當成只是沒有生命的細胞組織或生化材料。他們應受到極謹慎的尊重與保護,即使這並不是說,他們應受到絕對的保護。
現在所使用的方法常違反尊重生命的原則,因為他們大部份必須在體外受精,而體外受精的死亡率很高,許多合子不到桑葚胎的階段就會死去。臨床上為保證成功率,往往培養過多的受精卵,再從中「優生」挑選好的胚胎植入母體,或者將「不夠健康」的丟棄。植入之後若存活的胚胎仍太多,還會進行「減胎」手術,將「不必」要的胚胎加以移除。這些技術很顯然是不夠充分尊重胚胎的生命。無論如何,醫師或者不孕夫妻應避免使用會傷害初期人類生命的人工生殖方法。醫師尤其有責任將所使用技術的利弊得失,充分告知受術之夫妻,使他們能夠選擇符合倫理的方法。
4.不可將代理孕母商業化。
表達感激的必要報酬是無可厚非的,然而,以報酬為主要目的的代理孕母卻容易引發許多嚴重的問題。今天臺灣社會連保母給受託嬰兒灌食安眠藥的案件時有所聞,一旦代理孕母商業化,將很難杜絕代理孕母只為了錢,而將胎兒或自己的身體工具化的風氣。另一方面,許多女性主義意識的人已經開始擔心,商業化的代理孕母容易演變成有錢婦女對貧窮婦女的經濟劫掠。
醫療問題
臺灣婦產醫學醫療化的結果已經可以說世界第一︰我們有世界第一的剖腹產,子宮切除、性別鑒定也聲名在外,這樣的第一除了恥辱,還有什麼?未來試管嬰兒式的代理孕母一定包含性別鑒定,而且會比剖腹產更多醫療控制。
醫學將不孕的事實當作是「病」,代理懷孕因此也就成為不孕症的治療方法之一。醫學對檢查及治療「不孕」所帶來的屈辱、痛苦完全不經心,也毫不猶疑利用另一個女人的身體。在這次的代理孕母的適應症討論中,還包括︰糖尿病、洗腎、心臟病等病人,雖然後來因為怕浮濫而擱置,不過即使這樣的討論,也足夠讓人心驚膽顫為醫療的極力擴張捏一把冷汗。
如果運用一些想像力,將來說不定會有專業孕母出現,有錢、怕痛、或愛有好身材的女人就可以不用自己懷孕了。制定法律要有前瞻性,這樣的想法不能說完全匪夷所思。現在不就有女人為了討好先生、保持陰道的緊張度而剖腹生產?而我們的不肖醫生也會為她們千方百計想出剖腹生產的合法理由,結果造成世界第一的剖腹產,由此可見以上的說法不完全是危言聳聽。
代理孕母合法以後,醫生切除子宮可以更不小心了,說不定還會有人故意切除子宮以符合代理孕母的要求。
早期的生殖科技討論,即使所謂的人性關懷也只討論到人倫關係,而從來沒有涉及女性權益。在醫生及科學家的小圈子裡,女人被視為研究、討論、試驗及工作客體,而不是有主體性的個人。早期的科學家們討論胚胎、生命、宗教、社會,就是沒有討論過女人、用作試驗的女性身體、以及控制人類生殖就是控制女人懷孕及生產這樣的事實。在法律案件的爭議上,根據的是兒童權益,而非女人做為母親的權益。
遵照醫學倫理人體器官是不能出售的,但是在9月27日的公聽會上,卻出現︰「子宮不是生產用的嗎?空著不用幹嗎?」的聲音。人體器官有許多是儲備的,是不是也可以用同等的論調租借給他人使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為什麼輪到女人的子宮就可以例外了呢?
對Whitehead的案子裡,國外的女性主義者提出他們的看法︰Whitehead案實際上等於是生父與生母爭監護權,但是當時所有的媒體都稱Whitehead代理孕母,而稱呼Stern「生父」。在爭取孩子的時候,這樣的稱謂,對Whitehead不利。而且依據媒體的報導似乎 Whitehead 既出租子宮在先,又背信於後,所以在聲勢及輿論上一開始就輸了。對這個案子的結果Rita Arditti(1987)說︰Whitehead 案讓人覺得孩子只有一親,並非雙親,而那一親,便是父親。
女性主義者除了關懷母權、女性身體自主、婦女健康之外,還關心母職、「母親在法律上的人格被分隔的狀況。生殖科技使得母親被分裂為︰基因的、生物遺傳的、社會的;懷的、生的、養的等各種形式,母親的人格完整性消失。尤其是代理懷孕更使得婦女的身體被濫用、尊嚴被踐踏,女人被物化淪為孵卵器、保溫箱。在立法院的公聽會上有人說︰如果不用代理孕母而使用代孕者的稱呼即可免去未來雙方爭奪孩子,更是物化及藐視人性。這樣的作為只可能替法律省事,強化醫療及法律霸權,卻完全破壞了懷孕生產的神聖性及母子間親密連繫。
宗教觀點
佛教
子宮商品化加劇女性苦難,借子宮變成是替胎兒『租保溫箱』,身體的一部分既可作為『零件』以標價利用之,那麼任何商業性的器官移植有何不可以?
佛法的『緣起論』作邏輯推演,生命縱使不必然要說成是『神聖的』 但同為『關係性存在』的生命,卻是不分尊卑而一律平等,因此也是無價。器官商品化,自然會導致窮人,弱者的器官成為富人、強者所覬覦的零件;代理孕母的子宮租賃,縱使來自當事人的兩廂情願,但這是否也意味著生殖科技導致弱勢女性的苦難加劇?
由此看來,『代理孕母』之類生殖科技的發展,不宜純粹定位為『不孕夫婦誕生新生命的福音』而是人類在『後有愛』的本能驅動與文化訓練中,以貪瞋癡互相角力的產物。在這場角力中,科技戰勝生命,父權意識的迂迴戰略成功,孕母與受精卵都成了『工具』或是『配件』。
醫生否認自己扮演了『吹皺一池春水』的上帝,他們只是『回應不孕症者的禱告』,卻只因『受精的雛兒不會禱告』而心安理得活活掐死他們。
追根究底,連『孩子非要是己所從出不可』的觀念,都是『無明』的表現,亦即是自我感的發展。那麼,佛法對於『代理孕母』,又豈能發出歡愉的讚歎?
基督教
對於深受未能自然生育一事困擾的夫婦表示無限的同情,也深深了解他們期待借用現代生物科技來解決問題的願望,甚至也不全然反對他們這樣做,我們祈求上帝的憐憫,安慰常與他們同在。然而,我們也要很誠懇地呼籲這些家庭和社會共同面對更大的問題,就是整體人類生命的問題。
我們深信上帝願意也喜歡我們運用智慧和科技來改善人類的生活,但是我們也確信人工生殖技術的運用不應該是無止盡,沒有限制的。固然,嬰孩的出生應當尊重父母親的抉擇,可是我們也認為一切有關嬰孩的抉擇必須是謹慎和負責任的。就此而言,我們認為『代理孕母』的做法不但不能保障母親的生命,更不能保障胎兒和嬰孩的生命。例如:一旦代理孕母對於懷孕一事的想法與委託人的想法相異時,是誰有權做抉擇?這涉及倫理抉擇的準則之一。代理孕若以為胎兒會危害孕母的身心健康,而委託人卻不以為然時,那要怎麼辦?代理孕母若勉強繼續懷孕,對於胎兒和將來要出生之嬰孩的生命會有甚麼影響?這是攸關公義與仁愛的問題。無論是母親或胎兒,嬰孩的生命的尊嚴和權益,都不應該受到某一種特定法律的危害。還有,我們是否也需要考慮代理孕母的丈夫的生命在此過程中所受到的影響?這是關於一個家庭整體生命的平安和和諧的問題。
基督教會深信人的生命具有上帝的形像,生命的開始和成長都應該關懷人性,尊重生命的尊嚴,『代理孕母』所衍生的倫理問題很多,諸如委託人在選定孕母的過程中,孕母實際上已成為生產的工具,或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已;『代理孕母』會使母親和嬰孩成為商品;母親接受金錢,嬰孩交到別人的家庭;這不但涉及人與人,雙親與子女關係的疏離與物化,也跟一般公義,仁愛的倫理準則相違,這都是基督教會無法苟同的作為。我們以為這不只是法律的周全與否,更是人性的尊嚴的問題,我們不能接受使人的生命走向『物化』的法律。
我們政府應該積極努力的不是訂定『代理孕母』的法律,而是積極協助各大醫院成立醫療保健倫理諮商委員會,讓人民在面對醫療事務所引發的倫理困境時,能有所請益,而非茫然無助。我們也應該積極培育醫院的社工輔導和協談人員,使他們更可以幫助前來求診病患的心理問題。譬如說,我們能否協助一對夫婦明白不生育並不一定是不美滿的婚姻和人生?我們如何使不孕的夫婦脫離傳統文化對不孕之看法的束縛與壓力?特別是讓社會大眾從『生育才是女人』的迷思中醒悟過來。
基督教對於人生的看法是生命應該展現仁愛、公義、和平。人,無論是個人或團體,社群,所有的行為:從動機、目的、和實際作為,都應該以仁愛、公義、和平為圭臬。我們從目前『代理孕母』的法律條文和立法用意,看到的卻是反映少數人對自身利益的關心,忽略甚至危害了整體的生命,這絕不是仁愛、公義、和平的社會所應有的態度.因此,我們對於目前『代理孕母』合法化一事,表示反對的立場。
女權主義
女性主義者反對代理孕母的原因,大致來自於三個對父權的激進反判:1.打破血親連帶始能締造幸福家庭的迷思、2.拒絕將女人化約為生產機器(mother machine)的意識型態、3.反對自由契約至上的資本主義邏輯。
1.打破血親連帶始能締造幸福家庭的迷思
國內外的女性主義者都一致地將收養視為是解決不孕的最佳選擇。然而,荷蘭兩位女性主義政治學家卻指出,片面要求不孕者收養的說法,一方面忽視了很多國家在收養問題上所做的諸多限制,另外, 這種『理所當然』的收養論,顯然也是有選擇性的。因為,它只是用在那些生殖器官無法『正常』運作的婦女身上,而不適用於所謂的『正常人』。
領養,當然是一個解決不孕的可能選項,但不應該、也已經不可能是唯一的選項。血親迷思固然是女性主義應該批判的對象,但沒有理由片面要求不孕婦女一肩扛起這個重擔。其次,代理孕母、捐精、捐卵等人工生殖科不僅無法維持純粹的血緣關係,反而將嚴重衝擊傳統的血親主義。例如,在受術夫妻純粹透過捐精、捐卵受孕生產的情況下,決定法律上親子關係的基礎不是血緣、基因,而是誰購買了精子、卵子。至於,在代理孕母的情形下,在部份代孕(孕母提供卵子並代孕)時,法律上的母親也不以血緣為基礎。理論上,甚至會出現受術夫妻沒精、沒卵、沒子宮,於是透過捐精、捐卵,再交由另一婦女代孕的情形,如此一來,生出來的子代,根本和這對夫妻完全沒有任何血緣上的關聯。無怪乎,Stanworth要說,人工生殖科技將置基因上的親職於險境。
2.拒絕將女人化約為生產機器
Shulamith Firestone將女人的生物性的生殖能力,視為是女性解放的障礙,主張「應藉由各種可能的方式,將女人從其具生殖的生物性中解放出來,並將生產以及育兒的角色擴及到整個社會,男人以及女人身上。」Firestone在七○年代,驚世駭俗的提出人工子宮的解決方案,看來已為時不遠。
代理孕母合法化經常面對的嚴厲質疑是,此一生殖科技的使用涉及另一個女人的子宮,以及另一個小孩的出生。於是代理孕母被部份女性主義者視為將女人化約為子宮的極致表現,同時,透過代孕契約,貧窮女人更是無可救藥的淪為有錢女人的生產工具。代理孕母契約一旦透過國際市場的交換機制,販賣女人(子宮)與小孩的行為將很快地被國際化。Andrea Dworkin更將代理孕母比擬為『生殖娼妓』,代孕者好比妓女,醫生及科學家則有如皮條客,並指男性霸權控制女性生殖的結果,將造成女人的人間煉獄。激進女性主義者認為女人在父權體制下,早已內化父權語言,並習於服從男性的慾望與需求,根本無由掌握自己的身體自主權。同時,在社會普遍教育女性要充滿愛心與協助他人的情形下,女人自然傾向於幫別人懷孕。就如同,娼妓不是天生的,而是社會創造的一樣,代理孕母也是社會型塑出來的,女人被教導她們比男人來的大方,願意與他人分享她們的所有,包括她們的身體本身。
代孕者究竟是不是被物化,實關乎代孕者的主體性,而不應由旁觀的女性主義者來定義或代言。事實上,已經有代理孕母現身表示,自己確實在經濟困窘的情形下為人代孕,同時,如果還有機會也願意再做代孕者。也有婦女在女性主義大嚷代理孕母物化子宮的公聽會上表示:「我不懂女性主義,但是如果有人需要我的幫忙,我願意當代理孕母。」
有趣的是,激進女性主義者一方面大力批判代理孕母物化女人時,另一方面,她們也為代理孕母將引發傳統母親身分斷裂的危機感到無比的焦慮。激進女性主義者Gena Corea認為,人工生殖科技已讓女人淪為純粹的生產機器,使得生殖過程將如同一般商品的生產模式一樣,被切割成幾個破碎的片斷。她語帶嘲諷的指出,「未來也不再出現同時給予基因、又孕、又養的母親。相對的,將來基因狀況優的女性將貢獻她的基因,再透過人工受精讓身強體壯的女性來懷孕,最後找個好脾氣的女人把它扶養長大」。然而,在Corea近乎不屑的嘲諷中,我們卻也看到代理孕母在理論上足以顛覆三合一母職概念的激進潛能。事實上,Corea等激進女性義者甚至將這樣的理論潛能推至極致,認為人工生殖科技的出現將解構母職的概念,並將摧毀被視為女人認同基礎的生殖活動。林芳玫也指出這種斷裂的生殖過程否認了母親是人類的起源;母親不是完整的、有自我主體性的個人,母親被碎裂成不同的生理器官、組織與細胞。醫學界取代了母親,成了生命的起源與創造者。不同女人的卵子、荷爾蒙、子宮就成了醫生創造生命原始材料。
然而,Corea這種強調將生殖視為女人的認同基礎,以及林文強調母親身分的完整性與同一性的批判,似乎又要將女人重新導回那個女性主義對抗許久,強調女人傾向於『養育、自然』,並高度重視自然母性與自然生殖的本質論上。事實上,所謂母親被碎裂成不同的生理器官、組織與細胞,其實就是母親身分的多元化。然而,即使沒有代理孕母,但是離婚率以及再婚率的升高,母親身分多元化(一個小孩可能有生母、養母、繼母、乾媽等)的現象,也逐漸為一般人所接受。
因此,真正的關鍵在於這些母親能否和小孩有良好的親子關係,而不在於她們(養母/繼母/乾媽)是不是生了她/他,或者所謂的生母用什麼方式懷了她/他,又用什麼樣的方式生了她/他。
其次,Gena Corea雖然宣稱,母親身分的斷裂使得『生物性母職成了多餘』,但是,父權社會強加在女人身上,要她們負擔起賦予生命、又孕、又養的三合一母職觀念,不也正是女性主義者長期以來不斷在挑戰的意識型態嗎?到底婦運是要追求一個個被生/育子代累的面貌模糊的三合一母親,還是要讓女人自在的選擇要在什麼時機,在什麼樣的層次上當母親(例如,捐卵媽、懷孕媽、奶媽、法律上的媽、二媽、乾媽等等),和她的『子代』維持一個什麼樣的關係?事實上,父權社會絕對遠比諸多激進女性主義者更願意歌頌母性或自然母職的偉大,因為,如此一來,只提供精子的男性,得以真正和生/育子代的再生產勞動保持更高度的疏離,而耐操、耐磨、逆來順受的三合一母親則成為再生產勞動的不二人選。
3.反對自由契約至上的資本主義邏輯
代理孕母契約的完成通常是以代孕者在生產後義務交付該名子女,而尋求代孕者則相對必須給付相對報酬,因此,此類涉及交付子女/給付報酬的契約常被指為買賣嬰兒的契約,Shanley甚至將代孕契約比擬為黑奴的賣身契約,Raymond則認為此類契約實以女人的身體為工具,目的是用以滿足私領域中男性的生殖需求。
截至目前為止,各國對於此類涉及交付子女/給付報酬的代孕契約在法律上能否被強制執行大都持保留態度。就法律效果而言,美國新紐澤西州即主張不予強制執行,但也不予處罰,所以如果代理孕母拿不到約定中的報酬,公權力不會介入;代理孕母不交付小孩,公權力也不會強制她交付,至於小孩的監護權則由法官依「小孩的最佳利益」來決定。有的國家則進一步以刑罰規範涉及第三者仲介或以金錢給付為代價的代理孕母契約,例如,英國1985年代孕安排法明文禁止商業代孕,任何仲介商業代孕者,以及接受刊登類似『子宮代僱』廣告的報業、期刊、廣播電視系統的發行人、負責人、經理人都要予以處罰,但不處罰代孕者或尋求代孕的夫妻。美國密西根州更將代孕理母仲介者列為重刑犯。
主要考量在於避免子宮被物化、商品化,但是這樣的禁令,一方面遠遠悖離現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主流社會關於『工作』與『母性』的意識型態。
自由主義國家要求代理孕母無償代孕的一大關鍵在於──不希望、也不願意將代理孕母視為一種『工作』,它可以是女人義助女人的慈善行為,值得容忍甚或贊揚。事實上,『工作』是在男性中心的狹隘經驗下被定義的,諸多以女性為主的再生產勞動始終沒有被認可為是可以要求支領報酬的『工作』,例如:生產、育兒、燒飯、洗衣等家務勞動,主流社會人人喊打的性工作,以及代理孕母等等。女性主義者不斷地爭取家務有給,強調家事勞動就是工作的概念,卻始終沒有得到主流社會真誠的回應與接納。然而,媬姆或菲傭卻讓我們看清楚家庭勞動的價值;性工作者的性交易也讓我們看見,「良家婦女」在私領域中,經常必須配合丈夫進行性行為的「性」處境;代理孕母則讓我們看清楚,父權社會把女人從受孕、懷孕到生產這一連串長達一年,必須歷經害喜、擔心流產、頂著龐大肚子行動困難、不斷進出醫院產檢、擔心懷了畸型兒、歷經產痛,再慢慢地等待身體復原的艱辛過程視為女人的「天職」。
其次,如果我們將涉及金錢給付的商業代孕與利他主義的代孕放在一起來看,自由主義國家或主流社會真正關心的,不是子宮被物化,而是女人在懷孕這件事情上,究竟有沒有逾越性別規範或框架。
Sharyn Roach Anleu在比較了社會大眾對美國1985年著名的商業代孕契約Baby M 案,以及1988年澳洲維多利亞省,一位姐姐義務為無法懷孕的妹妹及不孕的妹夫懷孕的案例時指出,澳洲媒體及社會輿論一面倒地贊揚姐姐的義行,其實是因為姐姐的代孕行為完全符合社會對女人的性別規範:要求女人重視愛心、利他、養育與關懷,而不是懂得計算自己的利益、關心自己的權利,而輕乎母性的女性角色。就如同在Baby M 案中,新紐澤西的法官在裁定受術丈夫是否能領養這名小孩時所宣稱的:「當她(代孕者)在簽訂這個契約時,她就已經選擇了放棄當母親的權利。」法官的話指出主流社會將母親那種 『無私無我的母性』必須與金錢交易劃清界線的社會規範,也正是這樣的社會規範,讓同時也是提供卵子的代孕者Mary Beth Whitehead受到美國社會輿論的責難。
禁止代理孕母收受費用幾乎是舉世皆然,但是這種希望透過不給付酬勞以對抗商業化的道德主義式的思考,顯然只是針對代孕母的片面要求,因為整個醫療界透過代理孕母而大賺其錢的商業化現象被徹底的忽視。
很顯然地,自由主義國家在嚴禁代理孕母收費這一問題上,出現二個盲點:一、物化女人自己的子宮不是問題,只要不涉及賺取大筆金錢的自利動機。二、透過子宮賺取大筆金錢也不是問題,只要這些錢不是進入代孕者的口袋。